一下火车,踏上上海的土地,活像一群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在繁华大都市的陪衬下,我们这帮穷学生,一个个土的都快掉渣的土包子,如果不是身上揣着学生证和学校开的介绍信,准被当作民工。
来不及欣赏美丽的上海夜景,我们就直奔下榻的“酒店”。带队老师早来了两天,已经安排好了,大伙一个个找到了自己的房间,唯独我和大头成了“孤儿”,找不到自己的房间,大头瞪着驴眼把名单瞅了一遍又一遍,就是找不到我们的名字。带队老师拿过名单,扫了一遍,“哎呀。还真把你两给忘掉了。”
“我操,两大活人,又不是两陀屎,屁眼一松就给漏掉了。”大头趁老师一转身,就开始嘟囔开了。
“去你先人的。你才是一陀屎呢。”我对大头的这个比喻十分反感,我趁机擂了大头一拳。
很快,带队老师给我们安排在三楼的房间。我和大头说说笑笑的进了房间。环顾了一下房间,条件还不错,电视,空调什么都有。我们还正想呢,这个条件不像学长们所描述的嘛!
吃饭的时候到了。大家唧唧喳喳的说个不停。就听大家抱怨说,条件不好,冲凉人多十分不方便。
“你们这帮人渣,要求还真不低,出来实习能住这个条件就不错了,咱的,你们还想住星级酒店?”
“几十个人就一个冲凉的地方,多难受呀?”不知道谁嘟囔着。
我纳闷了,“房间里面那个小门推开不就是洗手间,可以冲凉的吗?”
“冲个鸟呀。推开门就是别人的房间了。”
吃过饭,回到住处,我和大头才恍然大悟。原来一楼和三楼的房间真是有天壤之别,一楼的房间潮湿阴岸,几个上下铺一字排开,床板硬的能当面板。房间里根本没有洗手间,只有一个破烂不堪的风扇,打开就像直升机,摇摇欲坠,在下面要提防着别掉下来把人的脑袋削掉,最要命的是就这还经常罢工,时不时就不转了。冲凉集中在一个地方,男女共用。
和我们上面一比,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,难怪大头一进门扭头就走,还以为走错了,"妈的,怎么跑到渣滓洞里来了。"
我和大头乐了,看来我们是因祸得福,才得以享受和老师一般的待遇。不过,我和大头没有忘记兄弟们,一声招呼,大伙跟着上我们房间冲凉去了,看着这帮受苦受难的兄弟,我和大头都觉得他们怪可怜的。
“唉。我说大头,你说我们住这里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呀。”
“没关系。明天你俩就和他们一样了。”不知道啥时候,老师像幽灵般的出现在我们身后。
我和大头轰然倒床!
第二天,我们就浩浩荡荡的杀向工厂,老师让我们自己带队过去,说是工厂有人专门接待。到了厂门口,倒是真有一个人等着我们,不过,那个中年男人操着正宗的上海口音,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涉,他才搞明白我们是哪个学校的。
就这样,我们领了工作服,安全帽,开始了我们的实习生活。一开始,还蛮新鲜,过了两天,才发现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莫过如此。
我们一行八人被分配到了一个小组。每天,我们还像老师说的那样,按时上下班,和工人师傅们一样。可是,我发现从一开始工人师傅们好像就不怎么搭理我们,包括被分配带领我们的那个师傅。上班第一天,就和我们说了一句话,他把我们几个带到主控机房,指着一个四方的大铁桌子,“你们就坐这里吧。”这句话还是我们连蒙带猜才搞明白的。
师傅撂下这句话,就忙自己的去了。我们八个就像开联席会议一样,分列而作,呆呆的坐了一天。晚上回去和别的组一交流,情况都一样。“TMD,工人师傅就当我们根本不存在!”公公愤愤不平的说。
老师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以后,告诉我们说,你们必须要主动学习,虚心向工人师傅们学习,要做到不耻下问。可是,我们的主动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,工人师傅们对我们的问题,不知道是太深奥了,还是咋的,无法给出一个明白的回答。后来才发现,很多工人师傅只知道怎么操作,而不知道原理,更多的师傅是不屑和我们这些小屁孩废话。
我想我们小组的那个师傅可能是后者。就这样,我们几个人就那么干坐了一个星期。早上一来,坐在那里就盼着下班,下午来了就盼着下午下班。其他事情又不能做,为了保证我们大学生良好的形象,我们要严格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。于是我们就不能随意走动,聊天,打打扑克,看看小说的事情也只能是想一想。
“妈的,我们怎么成了坐台小姐?”大头突然间崩出来这么一句。
大头的话自认引来男生们的一阵窃笑(不敢大声笑)和几个女生的强烈抗议!
有次,大头闲的实在无聊了,就跑去开了一下空调,谁知道那个空调是整个工厂的空调,出风口有火车头那么大,结果师傅一进来,冻得发抖,并且告诫我们不要乱动开关。
事情出现转机是在那次一个领导的意外发现。那天,我们像往常一样静坐着数对方的鼻毛。正在那时,办公室门开了,进来一个小老头,从他那吃惊的眼神可以看出,我们还是给了他一些意外。
他疑惑的盯着我们看了半天才说话,“你们不是工人吧?”
切!是个人都能看出来,哪有工人会像我们这样穿着崭新的工作服,戴着发亮的钢盔,像个菩萨似的坐着。
“我们是来实习的大学生。”
“是谁带你们实习?”
说实在的,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带我们师傅的姓,我们只好指了指里面的那个屋子,“那个师傅”
“他人在哪里?”
“不知道。”
老头子问完,转身走了。我们确实不知道师傅的行踪,师傅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去哪里,凡是有人来找他还是电话找他,我们的回答永远是不知道。
第二天,奇迹发生了,一上班,师傅竟然主动和我们说话了。后来,我们猜测,昨天问话的那个人可能是个什么领导。师傅不知道从那个嘎拉角落里抱出来一摞资料,上面的灰足有半尺厚,师傅扔下一句,“你们自己看吧”又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“我操他妈的,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资料,一本能砸死一头牛!”大头一边说,一边在目测这个书的厚度。对面不知道谁卯足了劲,撅着屁股,想把上面的灰吹掉,可惜屁都整出来好几个,灰倒是没吹掉多少,吹掉的一些也全跑到对面同学的脸上,活像涂了一层厚厚的粉。大头最可怜,只剩个眼珠在咕噜咕噜的转。要不是在工厂里面,肯定又会爆发一场世界大战。
过了两天,师傅过来告诉我们,你们早上十点钟来都可以。实际上我们是八点上班。
“不行呀。我们老师要来点名的。”一个女生回答。
师傅又说了,“没关系,等你们老师来了,我就说你们下生产线了。”
认真的女生连这些话也写在了实习日记中,实在是没啥写的。
师傅的话无疑对无聊的我们是一个解脱。
起初,我们都以为师傅真好,看到我们实在无聊,替我们想办法。后来才发现,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。
试想一下,八个无聊的人,大头无聊到极点抠一陀鼻屎也能当橡皮泥玩半个小时,面对这些比圣经还老的资料和那些冷冰冰的庞然大物,唯有那个师傅能引起我们的一点兴趣,于是师傅的一切都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,师傅什么时候来了,什么时候走了,什么时候接电话,什么时候有人来找过他,这些都是大家看在眼里,想在心里的。
师傅不在的时候,大家就发言积极讨论这些问题,“你说师傅屋里那个床是来干什么的?”
“睡觉的呗。你没看咱这个师傅一点都不忙,机器正常运转的时候,就没事,躺在床上还可以睡觉。”
“我估计师傅平时都要睡几个小时,咱们来了他就不方便睡了,所以叫我们十点才来上班。”
“就是!就是!”几个没大脑的家伙就是喜欢附和。
“据我分析,来找师傅的这些人中,有个女的频率最高,我估计跟师傅有一腿”大头神秘兮兮的说。
“我看也是,那个女的还有点姿色。”
.................

这帮畜生在大头的带领下开始你一言,我一语的开始瞎扯开了。本来是实习来的,结果搞成了小说创作了。
不过,在我看来,师傅从起初的不愿搭理我们到了开始厌烦我们的地步了。什么原因不得而知,是不是大头他们那样分析的,只有师傅自己知道,但是师傅对我们的态度确实发生了改变。
临近奥运会开幕了,我们正盘算着怎么开口给师傅讲,让我们早点下班回去看开幕式。没想到,在开幕式前两天,师傅就告诉我们,奥运会要开始了,你们就不用来了,回去看电视吧。
我们一群人狂晕!看来师傅对我们的厌恶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。
其他小组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,木瓜所在的小组是最惨的一个。他们实习的地点是最远的一个,坐车都要40多分钟,每天中午下班回来,我们其他人都一觉睡醒了。可没过多久,我们就发现等我们回来,木瓜他们已经睡了一觉了,一打听才知道,这帮家伙坐厂里的班车,到了地方,连车都不下,直接再坐回来。我操,真他妈的绝!
不要看我们这群兄弟姐妹,实习一个个无精打采的,一到周末,大伙的精神格外的抖擞,几个热血青年带着矿泉水和干粮,准备徒步登上金贸大厦。得多亏了被保安拦住,不然我们班又得多几个烈士了。
大头不知怎么神经错乱了,说要去野生动物园看看老虎怎么吃人的。这么变态的提议竟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,于是一行人直奔野生动物园。到了地方,上车的时候,我看大头的脸色有点不对。大头问司机师傅,“这个老虎狮子能不能进车里来呀?”
司机师傅油门一踩,“不会的,绝对进不来!”
“那这一摊血是怎么回事?”
顺着大头的手指,只见一个座位的靠背上一摊鲜血。我靠,这他妈哪里是来看老虎吃人的,是来送死的吧。一路上我都这么想着,哪里还有心情去看老虎呀。
还好。虽然老虎吃人没看到,但也没有被老虎吃了,我们仓惶逃窜了回来。直到实习结束,那一摊鲜血还历历在目,虽然那个司机给了一个什么狗屁正常的理由,不过我从来没有相信过。
狼狈逃回大上海,就这么回去,也太没收获了,大伙决定去商场逛逛。
“欢迎光临!”我和大头还没走进,迎宾导购小姐甜甜的声音就飘进入了我们的耳朵。
大头的眼神擦着小姐的胸部而过,就目测出女人胸部的一切特征:诸如大小,形状,甚至手感,传说他的目测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准确率。
我们来到柜台前,一个小姐同样热情的招呼了我们。不过,大头问了一下价格,来了一句,“操,明抢啊。”虽然声音很小,但是还是让我听到了。
不过这时,另一种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只见木瓜和柜台前的一个小姐正在说话。
“Can I help you?”
木瓜挠了挠头(习惯性动作,我见一次打一次,他也没改掉这个恶习)用手指着柜台里面的一个东西,问,
.............
最后几句实在没有听清楚,我们把木瓜拉到外面,才放声大笑。我扯住木瓜的脸,仔细看了看,本来就是大胡子的他不知道几天没有刮了,野草似的胡子长满了大半个脸,难怪小姐愣是把木瓜当成了外宾招呼呢。
没过多久,木瓜又在地铁里又被误认为是爷爷,小朋友的母亲叫小朋友给这位“爷爷”让座,当时把我笑的差点岔了气。
在笑声中,我们结束了“意义重大”的实习。
写实习报告的时候,据传几百号人只有三个版本。当然了,我们班的是木瓜那个版本。实习报告成绩出来后,大家皆大欢喜,除了两个人。一个是木瓜,一个是大头。
木瓜的评语是:请用您的右手再抄一遍!!!显然,木瓜那狗爬一样的字让老师怀疑他是用脚写的,所以还在“右手”两字上面画个圈。
大头的评语是:请您把×××(木瓜的大名)的再抄一遍,两份报告一起交上来。原来大头这个SB抄木瓜的时候,连名字也抄了上去。老师知道大家都是抄的,但是为了惩罚像大头这种连名字都不改的人,惩罚他把两万字的实习报告重新抄过一遍,应该算是很轻的了。
于是,那两天,我们宿舍里面出现了一个壮观的场面:在摇曳的烛光下,两个赤裸的男人还伏在桌子上,奋笔疾书。大头一边写,一边还嘟嘟囔囔的,大头越写越气,忍不住写一个字,就给木瓜头上来一下,“都怪你他妈的那个字写的像屎一样,害的我受罪。”
大头写几下就要给木瓜来一下,木瓜最后也忍不住操了,“靠,你×的能不能换个地方敲呀,都敲水肿了!”
人在烦躁的时候,看什么都不顺眼,大头一会怪老头放屁了,威胁说要整个胡萝卜把老头的菊花堵住,一会又嫌公公磨牙声太响了,不过碍于公公的淫威,大头没敢做什么。大头一会捅捅这个的菊花,一会戳戳那个的脚底,那两天,整个宿舍人都跟着他俩活受罪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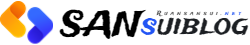





失落的羊5 个月前
研究插件:挂载点研究、文件读写研究、API读取数据、设置、前台显示
失落的羊5 个月前
今日申请十年之约博客成员!
失落的羊6 个月前
启用新的访问统计.
失落的羊6 个月前
重新整理长篇连载栏目
失落的羊6 个月前
构思公众号文章迁移计划